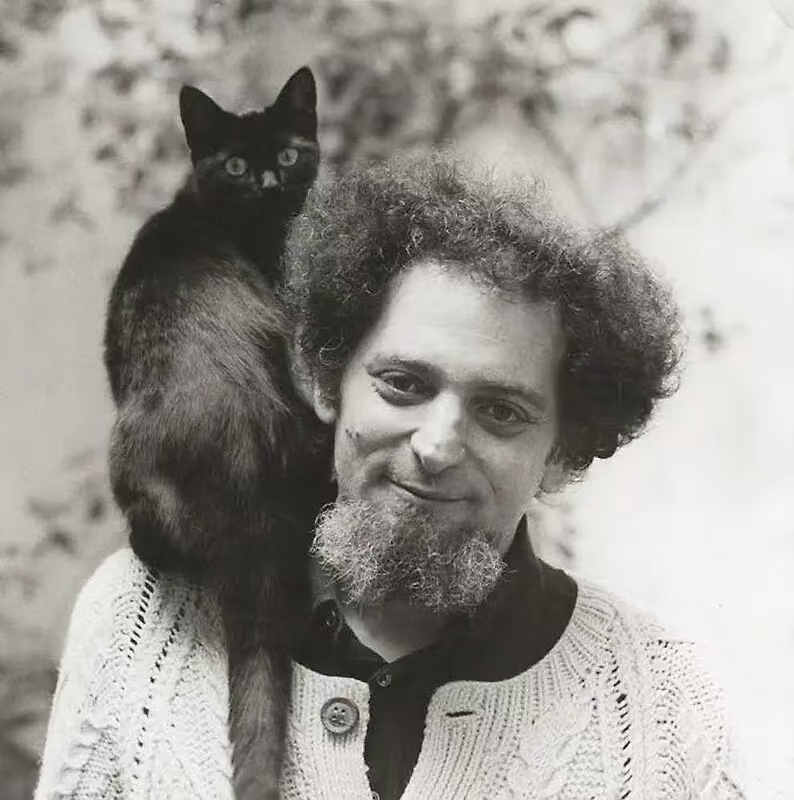城郊小路上的对话
城郊小路上,行人甚少,树林深处偶尔传出几声狗鸣。我与Z并肩而行,当时正谈论关于永生的话题。
Z:“在讨论的最开始,我们应该先谈谈“永生”这个概念的定义,尽管只有两个字,但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存在千差万别的内涵。”
我:“理应如此,按照我们所了解到的,可以进行简单的分类。一个重要的划分依据在于这里的永生是否有着终结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永生者可能能够长生不老,但是受到致命伤害依然会死去。”
Z:“这种类型在科幻小说中比较常见,海因莱因的《时间足够你爱》中的主角就是如此,不过他的长生依赖于小说中特有的回春疗法,简而言之就是换血。《海伯利安》中也有类似设定,诗人马丁依靠鲍尔森疗法活了好几个世纪,但只能延缓衰老,效果不如前者卓著。”
我:“看起来这种类型的永生与现实并没有一条鸿沟,衰老是生物的正常特征,在更高等的生物中更为显著,一些单细胞生物比如细菌在环境合适时可以不停地分裂而没有衰老的过程。人体的细胞有一个分裂次数限制,研究表明与端粒长度相关,也可能与一些氧化损失相关。现实与这类永生的差距不止这一个限制,一个人活得越久,得癌症的几率越大,一个癌细胞通常有好几个突变基因,DNA的每一次复制都有可能引入突变。”
Z:“从技术上说,这些问题很有可能被克服,更难解决的应该是伦理问题,不过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种类型的永生,姑且记为第一类永生,应该是最不容易遭受哲学家批判同时也是最受人向往的永生类型。”
我:“是的,第一类永生的关键就在于它并没有驱散死亡的阴影,只是将它无限推后。本质上讲,第一类永生者与正常人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尽管不同的寿命长度可能导致差异巨大的人生观念,但是他们都保留有离开人世的权利,一位哲学家确实找不到什么论点去攻击这类永生。换句话说,第一类永生者理论上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命长度,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必死的命运,这一点就足够吸引大多数人了。”
Z:“按照之前的分类标准,第二类的永生就是完全摈弃了死亡的概念,这里可以再细分一下,一种依然保留了衰老的永生,一种则是彻彻底底地长生不老。大概没有多少人对前者有兴趣,在文学影视作品里它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骇人的面目出现,大概形象就是一些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活死人,即使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正常人也比他们更有活力。例如托尔金的中土神话中的努门诺尔人,虽然他们寿命很长,但仍有竟时,即便他们踏上了永生者的国度,他们的生命也会像一片被不断拉伸的黄油,越活得久,越受折磨。《格列夫游记》中那些半死不活的人也是如此。坦率地说,这类永生几乎没什么讨论的必要,所以为方便起见,第二类永生就特指后者了。”
我:“很多哲学家都对第二类永生持负面态度,例如波伏娃的《人总是要死的》,里面的男主喝了一瓶秘制小药水后就完完全全永生了,不怕黑死病,不怕刀剑,不怕子弹。波伏娃大概是想说明没有了死亡,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博尔赫斯的《永生》其实也大差不差,荷马喝了永生之水,最后在虚无的摧残下喝了能够解除永生效果的水,回归死亡。”
Z:“所以哲学家们到底在批判什么呀?不应该拒绝死亡?还是不应该活太久?”
我:“我觉得他们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
……
散步结束后,我回到屋里照了照镜子,镜中影像与千年前无异。